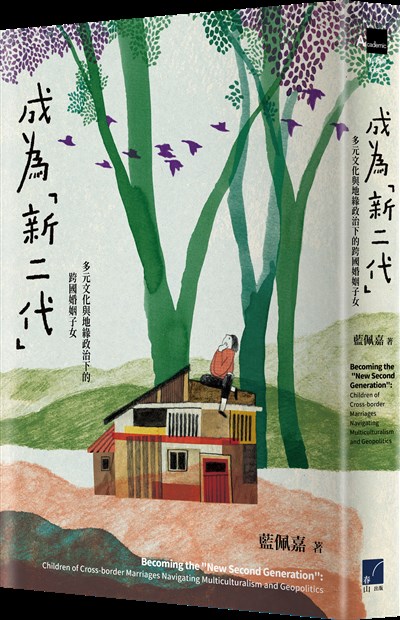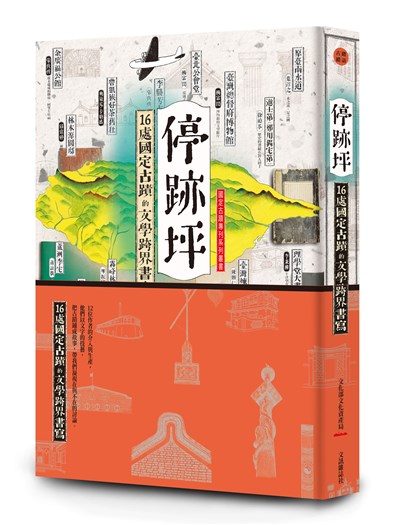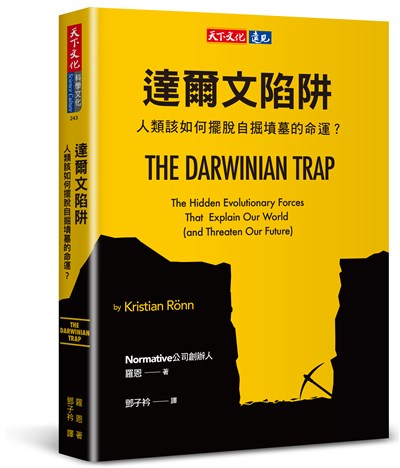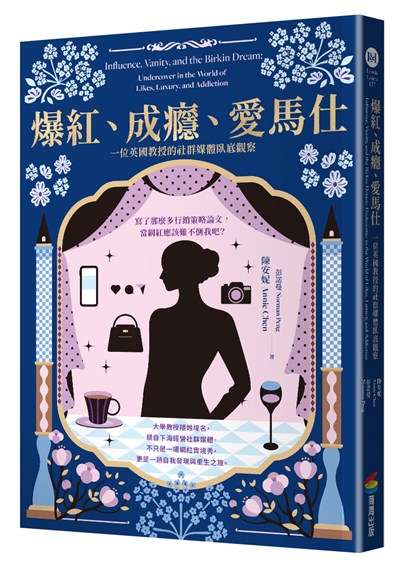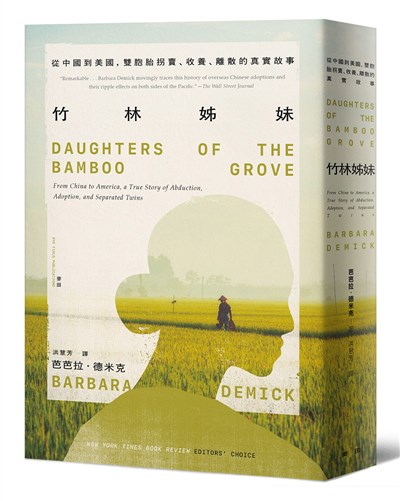
繼暢銷書《我們最幸福》、《吃佛》,獲獎記者芭芭拉.德米克最新力作,不僅提供了一扇窺見過去半個世紀裡瞬息萬變的中國的絕佳窗口,展示中國最惡名昭彰的政策所留下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講述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極權、由上而下的壓迫仍是德米克的核心關懷,新書中,她將從一對誕生於中國的雙胞胎命運,來探討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與跨國領養議題。
內容節錄
《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
史泰在摩門教會長大,三十多歲時,他試圖調和兩種看似矛盾的信念:遵循教會多子多孫的教誨,又要堅持自己激進的環保理念。他深信,零人口成長是避免地球過度遭到人為破壞的關鍵。與其再多生一個消耗資源的孩子,他認為收養才是更有道德的選擇。為此,他非常支持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一九九八年,他和妻子從中國收養了第一個女兒,隨後又申請收養第二個。雖然這段婚姻後來破裂了(主因是他決定退出摩門教),但二○○二年他仍以單親爸爸的身分再次收養一個中國女嬰。二○○四年,他與中國女性龍蘭再婚,不久後兩人又收養了第三個中國女兒。
史泰沉浸在身為人父的喜悅中,不禁好奇:自己何德何能,竟有幸成為這些乖巧女孩的父親?雖然他已不再信奉摩門教,但從小在教會培養的家譜研究能力,讓他對家族史格外熱衷。摩門教相信,信徒死後會與祖先團聚,因此在家譜研究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該教會擁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家譜檔案館。他們以縮微膠片和縮微膠卷的形式,保存了三十億頁的資料,儲存在恆溫控制、足以抵抗核爆的花崗岩山紀錄庫中。教會還創辦了非營利機構FamilySearch ;摩門教徒也創立了最大的族譜非營利機構Ancestry.com,總部設在史泰的家鄉猶他州李海市。
史泰對家族血統並不在意,但他很想了解女兒的親生家庭。他仔細研讀了大女兒梅琪娜的收養文件,看到上面記載著兩位在廣東省南部的路邊發現她的婦女姓名。二○○○年他前往中國時,請孤兒院安排他與其中一位見面。那位婦女告訴他,當時她和朋友聽到紙箱裡傳出微弱的哭聲,打開一看,發現裡面是個嬰兒,旁邊放著空奶瓶和幾張皺巴巴的鈔票。聽這位婦女如此詳盡地描述發現棄嬰的細節,他很感動。
後來,龍蘭回去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她是廣州的本地人,曾在白天鵝賓館正對面開一家紀念品店。當初史泰就是在她的店裡買畫時認識她的。龍蘭比先生更清楚當地的運作方式和人情世故,她找到了收養文件上登記的另一位發現者,最終問出了真相:她們根本與這個嬰兒毫無瓜葛。當初是為了幫助孤兒院,才同意在文件上掛名,後來又被要求重複最初的謊言,以安撫一位來頭不小的收養家長。
史泰後來在他的部落格寫下這段經歷:許多孤兒院的院長其實都面帶微笑地對你說謊,暗地裡想盡辦法阻止你了解孩子的真實身世和過去。他們會用孤兒院的車,載你到所謂的「發現地點」,指著某處說,孩子就是在這裡發現的,甚至找來當初發現孩子的人,描述當時籃子裡放著奶粉和衣物的情景。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你相信他們編造的故事。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那全是謊言。
二○○五年,史泰創立了Research-China.org,開始寫部落格分享收養的資訊,以幫助其他同樣好奇的收養家庭。他告訴我:「多數家庭對收養時拿到的資料感到滿意,他們收好文件後就不再探究。但仍有不少人想知道更多,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史泰後來變成許多收養家庭查找孤兒院資料、追溯孩子身世的重要資訊來源,也為我這樣的記者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在二○一九年獲獎的紀錄片《獨生之國》中,他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他的妻子龍蘭同樣是個鍥而不捨的調查者。夫妻倆首次合作的任務,是跑遍報社的檔案室,收購刊載孤兒院法定尋親公告的過期報紙。有時他們甚至得從廢品回收商的手中買回舊報紙。當年,這些尋親啟事在收養過程中並不會主動提供給養父母,但裡面往往刊登了孩子最早的嬰兒照。史泰夫婦後來把這些珍貴的照片轉賣給收養家庭。
起初,史泰夫婦以為這些尋親公告能提供孩子的身世線索,但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麼單純。他們把三萬則公告資訊輸入試算表後,發現太多巧合。同一天、同一地點發現的棄嬰實在多到不合理。這些孤兒院根本是敷衍了事,在文件上一再使用相同的發現地點和「發現者」來充數。
「怎麼可能在輪胎行門口發現十個嬰兒呢?只要你開始分析資料,就會發現那些都是瞎掰的。」我們第一次通電話時,史泰這樣告訴我。
我們第一次通話是在二○○九年,當時史泰主要關注的是像段家那類的販嬰案件。但後來他開始對湖南省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案件感到好奇。販嬰已經夠可怕了,但政府親手把孩子從父母的懷裡奪走,簡直是極端濫用公權力。目前為止,只有湖南省爆出的十三個案例得到證實,但他相信,這種事情絕不只那幾件。史泰告訴我:「政府企圖把邵陽事件描繪成個案,但我敢肯定,類似的事件絕對不止這一樁。」他鼓勵我深入調查,把其他的案件也挖出來。
我辦公室的一位中國研究員曾在社群媒體上看到一則消息,提到貴州也發生過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情況。貴州是個內陸省分,就在湖南的西邊,貧窮多山,石灰岩地貌的奇峰峻嶺導致交通寸步難行。當地有很多少數民族,例如與柬埔寨赫蒙族同源的苗族。和其他的貧困地區一樣,這裡也是送養嬰兒的主要來源地。二○○九年夏天,我和兩位中國同事輾轉搭乘飛機與火車,來到風光旖旎、依山傍水的鎮遠。正因地處偏遠,這裡才得以避開遊客如織的喧囂。傍晚時分,我們漫步走過古老的石橋,沿著河岸徐徐前行。河邊屋舍的陽台上掛著紅燈籠,天鵝悠然地游過燈籠印在水面的倒影。翌日天明,陽光照亮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貧瘠面貌。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車子駛離城區不過數分鐘,柏油路就沒了,只能沿著布滿車轍的土路往山上開。沿途顛簸,有些路段我們甚至得下車幫忙推車,才能勉強通過土丘和溝壑。遇到淺溪時,那位同樣希望事件曝光的司機主動下車,搬來石塊,在水面上排出一條剛好寬到能讓輪胎通過的臨時橋面,讓車子可以順利過河。車子在顛簸中行駛了近兩小時後,無法再繼續前進。我們只好下車,徒步穿越碎石遍布的山徑,前往我們的目的地:田溪村。那裡其實只有十幾間沿著山坡搭建的木造高腳屋,看起來搖搖欲墜,彷彿火柴棒搭成的。
儘管田溪村地處偏遠,也或許正因為偏遠,反而成了計生幹部鎖定的對象。他們沿著我們剛剛走過的同一條山徑跋涉而上,來搜查沒有戶口的嬰兒。村裡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孩子被強行帶走。我們最先拜訪的楊家,在二○○四年失去了六個月大的女兒,那是個意外懷上的孩子。母親楊水英告訴我們,丈夫在她發現懷孕的前幾天才剛做了結紮手術。夫妻倆原本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但孩子出生後,他們依然疼惜這個意外得來的小女兒,打算和哥哥姊姊一起把她拉拔長大。孩子們也都對這個新來的小妹妹疼愛有加。
楊水英對我說:「我們不會丟掉自己的孩子。生下來了,就會想把她養大。」計生幹部來村裡好幾次,每次都看見她背著嬰兒在田裡幹活。這些人極有耐心,像獵人般一直盯著,等待下手的時機。直到某天,他們趁她先生去鎮上工作、孩子都上學時,突然找上門來。計生幹部趾高氣揚地告訴她,法律規定他們有權帶走超生的孩子,而且不容許她提出異議。她坦承:「我不識字,根本不懂這些。」當丈夫陸顯德回到家,得知消息後,情緒崩潰,整個人失控,還拿刀子想自殺。至今他的脖子和胸膛上仍布滿了一道道明顯的疤痕。
這家人可能是我駐中國七年間見過最貧困的一戶。他們的木屋已經風化成洗衣板一樣的灰色,室內光禿禿的牆壁也一樣發灰。電力只夠供應一個懸在天花板電線上的光禿燈泡和一個電爐。他們家裡連一頭牲畜也沒有,只有一隻鴨子,卻執意要宰了那隻鴨子來招待我。陸顯德拿刀割了鴨子的喉嚨——或許就是當年他拿來自殘的那把刀——然後倒提著斷氣的鴨子來跟我說話。我的筆記本至今還留著當時濺上的血漬。當我們圍著矮桌吃午飯時,我幾乎難以下嚥,因為心裡明白,這戶人家平日根本吃不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