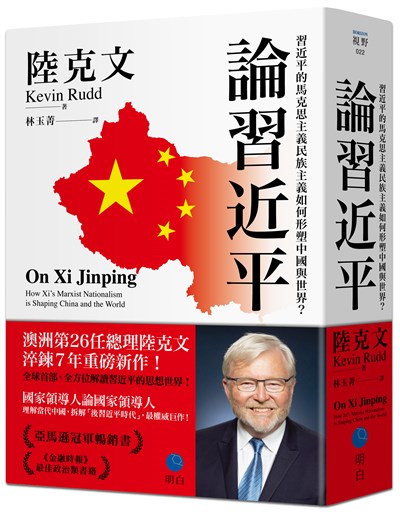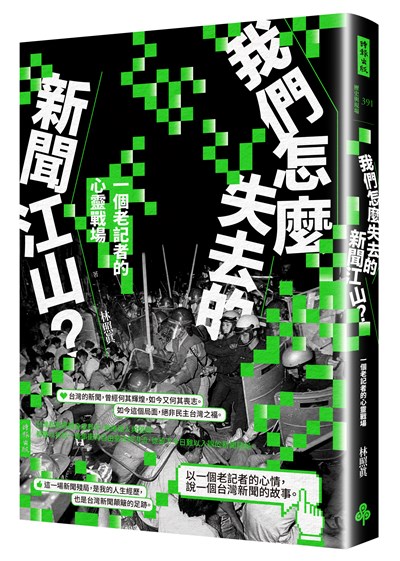
台灣的新聞,曾經何其輝煌,如今又何其喪志。
一個老記者以個人生命經驗,反思台灣新聞如何出現今日的殘局。
台灣的新聞故事背後,有兩股大洪流。先上場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場景,新聞自由是民主台灣最適當的隱喻;繼之而來的,是數位科技在全球引發的新聞輾壓,科技巨頭讓倔傲的媒體不得不低頭。
台灣新聞媒體身處其中,無論個人與組織,都難以抵抗一連串衝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難以入眼的新聞殘局。
這一場新聞殘局,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台灣新聞顛簸的足跡。
以一個老記者的心情,說一個台灣新聞的故事。
內容節錄
《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
新聞,我的一生!
每個人身上,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不僅關乎我個人,更與人人不滿意的新聞有關。
一想起「新聞」,我總覺得沉重。我知道新聞的世界沒有我,仍會繼續運轉。
我就是牽掛。
在課堂上談到有所感的新聞時,我感到自己的腎上腺素還是會往上衝。其實,我早已經不是新聞記者了。
新聞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工作。前二十年間,我是個新聞記者;中間加讀個博士學位。後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我是個新聞學者。
新聞工作讓我遇見人生百味,我的感受很強烈。新聞工作教我客觀公正,報導真實,這也是我為人的信念。新聞記者讓我每天都可以認識不同的人,見識不同的議題與事件。我像個雜家,在混亂中學習成長。
學者就不同。學者養成早有一定的規範,連一個錯誤的標點符號都禁受不住。學者最常作的事,就是在研究室內,折騰一篇篇自認為重要的論文。象牙塔內的世界,是塔外人毫無興趣的知識競賽。然而學術透析無止境的知識,讀書人會更謙虛,明白自己所知有限。也因為這樣,我對新聞,能有更多沉澱後的理解。
我即使是個新聞學者,身上常住的,卻是一個記者的靈魂。我的研究總會潛藏一股新聞焦慮;詮釋本是古典浪漫的新聞,如今為何傷痕累累。
「新聞」二字,是我人生的縮寫。我與新聞結緣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職業生涯即將來到六十五歲終點線。相較於球員高掛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儀式感,我這樣一個新聞人,寧可靜靜退場,讓這本書訴說內心想說的話。
我個人成敗事小,新聞大業才是我想談的重點。我在意的,是我視為志業的新聞,在我不再年輕力壯時,遭遇了前所未見的危機。
我在波瀾壯闊的民主洪流來襲時,加入新聞工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總覺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為學者的後二十年間,民主政治已經庸俗化,科技洪流來勢洶洶,新聞毫無招架能力,失去了光采,也失去了正當性。
我不知如何為新聞辯護,也無法給學生新聞依舊雄偉如山的承諾。
「我們是怎麼失去新聞江山的?」我問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在我記者、學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聞轉變的千絲萬縷。新聞變了,卻不是時間造成的自然轉變。
台灣的新聞故事背後,有兩大歷史背景,分別發生在不同世紀。二十世紀先上場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場景,新聞自由是民主台灣最適當的隱喻。二十一世紀繼之而來的,是數位科技的全球輾壓,讓倔傲的媒體不得不低頭,傳統的公共價值逐漸淡去。台灣新聞媒體身處其中,即使民主賦予新聞神聖光環,新聞仍然沉淪,徒留今日難以入眼的新聞殘局。
這一場新聞殘局,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台灣新聞顛簸的足跡。
記者這一行
這四十年間,新聞的變化太大,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想以一個老記者的心情,說一個台灣新聞的故事。
我還是初生之犢時,新聞是個數量稀少的行業。人們常說「老三台」、「兩大報」,就知道早期台灣媒體的數量並不多。那時的大學新聞本科也很少,政大新聞系就是我沒考上的第一志願。
新聞記者領薪水度日,會對這個工作起心動念的,多半是沒有發財夢、卻想經緯天下事的文人墨客。報社薪水還過得去,電視台的高薪則羨煞眾人。主播的家喻戶曉更挑動年輕人的表現欲,任誰都想擠進那個窄門。
新聞記者是我嚮往的工作,我尤其喜歡報紙。記者並非制式化工作,穿著可以隨性,說話不必官腔虛偽,讓我非常自在。一個記者負責一場新聞,我非常習慣一個人孤獨地完成工作。記者要有一定的抗壓力,才能讓故事立體成形,以真實的新聞面貌出現。
新聞因為記者的詮釋而出現,記者必須投入時間思考與寫作,讀者才可能理解。新聞講究真實,真實卻又有千萬種註解,全在記者衡量拿捏間。新聞的底線就是不能憑空捏造;不能明知為假還當真。新聞記者必須四處與人討論,整合出最逼近真實的說法。好新聞需要時間營造,記者要沉得住氣,讓別人願意跟你說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