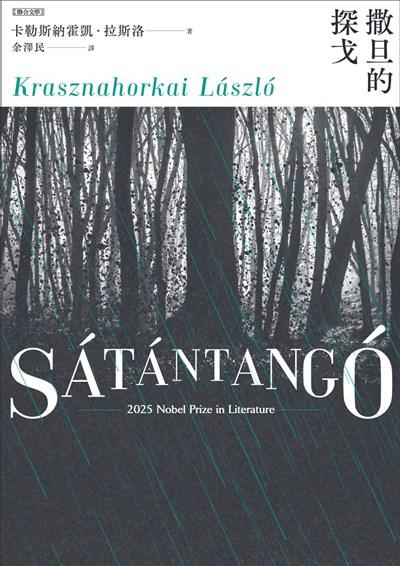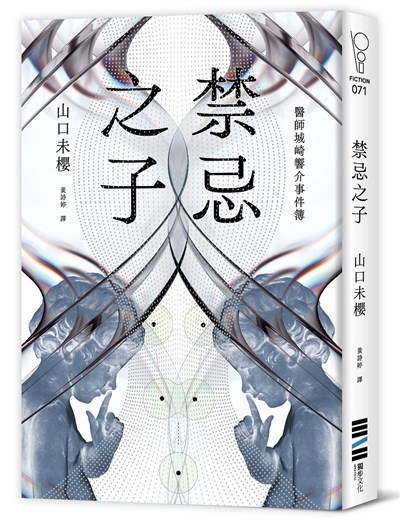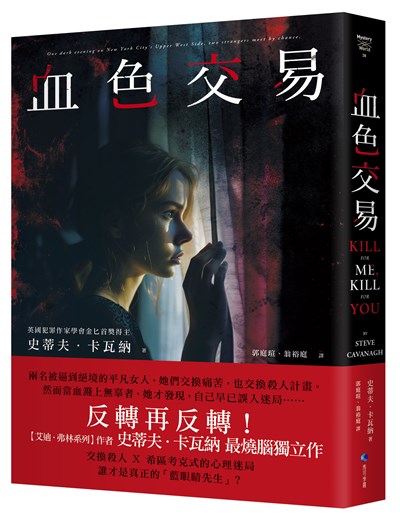小說家王安憶的作品被翻譯成英、德、荷、法、捷、日、韓、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是一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中國作家。她說,世事往往簡單,小說可不是,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考工記》以陳書玉為主軸,陳家「正宗清代古建築」大宅院為基底,輻射書寫動盪戰亂時期到新時代的二十一世紀,陳書玉與他的老宅、友人,一生的浮沉故事。
文章節錄
《考工記》
第一章
一
一九四四年秋末,陳書玉歷盡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慶起程,轉道貴陽,抵柳州,搭一架軍用機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彎入浙贛地方,換無數貨客便車,最後落腳松江,口袋裡一個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見路面盤桓電車軌道,力氣就又上來。抬頭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鱗次櫛比的天際線,一層層圍攏。暮色裡,路燈竟然亮起來,一盞、兩盞、三盞……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淚了。
二年前,隨朋友的弟弟、弟弟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哥哥、哥哥的同學——據說是韓復渠司令的侄系親屬,絡絡繹繹十二人,離開上海。去時不覺得路途艱難,每一程必有接應和護送。陳書玉沒出過遠門,中國地理也學得不精,並不知道哪裡是哪裡,只覺得很開眼。天地江河都是壯闊,漫野的青紗帳——他沒見過莊稼地,原來也是壯闊的。尤其入山西地界,車走在黃土溝裡,山崖上一道城牆,箭垛如同鋸齒,插入蒼穹,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氣勢。吃苦是難免的,食宿簡陋倒不計較,他最懼的是臭蟲。夜裡一吹燈,就聽壁紙與篾席沙沙的山響。蝨子也是一懼,這兩項甚至超過日本人封鎖區的可怖。也因為日本人的事不歸他管,自有負責的人。這一路也有月餘,說是避亂,更像遊山水,從仲夏到秋初,正值西南宜人的季候。許多年過去,方才知道一行匿身特殊人物,或者說,是為這一位特殊人物,方才集起這一行同道,所以如此順遂。以致回程中,時不時想起那一句舊詞:別時容易見時難。而他萬萬想不到,就因為此一行,日後新政府納他入自己人,得以規避重重風險。
邁過電車路軌,路軌沉寂地躺在路面,眼前彷彿電車的影,那影裡明晃晃的窗格子,閃爍一下,又滅了。腳下的柏油地,漸漸換成卵石,硌著磨薄的膠鞋底,他穿一雙元寶口的膠鞋,在多雨的西南可是個寶,到上海卻變得奇怪了。就在這一刻,天陡地沉下來,路燈轉到背後很遠的地方,街邊的房屋十之七八坍塌,間或一二座立著,緊閉門窗,沒有動靜。有人在瓦礫堆裡翻扒,咻咻驅趕野貓。一隻肥碩的老鼠從腳下躥過去,他原地跳一跳,放了生。廢墟上亮起一星點火,湮染開一圈,火上的瓦罐吐吐地小沸,有食物的香甜瀰漫在空氣裡,他吸吸鼻子,辨出南瓜的氣味。映著幽微的光,面前呈現一片白,這一片白彷彿無限地擴大和升高,仰極頸項,方搆著頂上一線夜天,恍然悟到,原來是宅院的一壁防火牆,竟然還在——從前並不曾留意,此時看見,忽發覺它的肅穆的靜美。他不過走開二年半,卻像有一劫之長遠,萬事萬物都在轉移變化,偏偏它不移不變。
從防火牆下走,順時針方向到西門,抬手一推,推不動。門上掛了鎖,托在掌上,沉重得很,是原先的舊鎖,又是一個竟然,竟然完好如故。停一停,退後兩步,張開雙臂,一臂扶牆,一臂扶牆邊柳樹,再原地一躍,兩腳就分別撐在牆面與樹幹,離地三尺,蹭蹭數步,又上去三尺,就到地方了。稍歇一歇,站穩,扶樹的手,慢慢移動摸索。某年某月,雷電正中劈開,都當它要死,卻發出許多新枝,養了許多洋辣子,大人孩子都繞道走,樹身且又長合,留下一個木洞,容得下一巢鳥雀,日後作了他家兄弟的祕處。
一番摸索,脊背就迸出熱汗,腦穴處則通電般一涼,摸到什麼?鑰匙!鳥雀都換了族類,可鑰匙原封不動。拳起手,握緊了,腿腳卻軟下來,溜到地上,站不起身,就抱膝坐著。這把鑰匙是叔伯兄弟幾個為各自晚歸設的約定。家中規矩,晚十點即閉戶,關前後門,此西門平素不進出,常年掛一把鑄鐵大鎖,於是,偷出鐵鎖鑰匙,私配一件,藏在樹洞內。都會的大家,子弟們難免沾染浮華風氣,夜間的去處特別多,不是說,海上升明月嗎?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硝煙未散盡,「薔薇薔薇」 就處處開了。離開上海的前一晚,陳書玉還在西區舞場流連,準確說,出行的計畫,就是在舞場裡做成的。
坐一時,喘息稍定,奮發精神,試圖站起,這才發現周身癱軟。發力幾回,立住腳,手索索地抖,鑰匙噠噠地碰擊鎖眼,就是對不準。天又墨黑,乞兒的篝火被阻在另一面,借也借不到。他懷疑是不是換過鎖或者鑰匙,正決不定,月亮跳出來,咔噠一聲,手底下一彈跳,就是它!推進門,抬頭望一眼,只見防火牆剪開夜幕,將天空分成梯形兩半,一黑一白,月亮懸掛在最高的梯階上,像一盞燈。
門裡面,月光好像一池清水,石板縫裡的雜草幾乎埋了地坪,蟋蟀瞿瞿地鳴叫,過廳兩側的太師椅間隔著几案,案上的瓶插枯瘦成金屬絲一般,腳底的青磚格外乾淨。他看見自己的影,橫斜上去,綴著落葉,很像鏤花的圖畫。走上迴廊,美人靠的闌干間隔裡伸出雜草,還有一株小樹,風吹來還是鳥銜來的種子,落地生根。迴廊仿宮制的歇山頂,三角形板壁上的紅綠粉彩隱約浮動。跨進月洞門,沿牆的花木倒伏了,卻有一株芭蕉火紅火紅地開花,映著一片白——防火牆的內壁。他佇立片刻,忽生一念,當初造宅子時候,周圍定是空曠無人跡,直面黃浦江,所以會有防禦的設置,就像歐洲貴族的城堡,那是什麼年代?他的歷史課和地理課一樣馬虎,也受實用觀的影響,目力之外,在他就是不存在。天井的地磚,覆了青苔,厚而且勻,起著絨頭,亮晶晶的。兩口大缸被浮萍封面,面上又蓋了落葉,青黃錯雜,倒像織錦。
他立在天井中央,看自己的影。這宅子走空有多時了,有在他之前走的,又有在他之後;有往南,有往西,還有往東——兩年中,他收到過父親一封信,途中不計經歷多少時間,多少不知名的地點,信中所寫都是遲到的消息。問他身在何處,境遇如何,妹妹們是否可去投奔。他沒有回覆,一來時過境遷,妹妹們早就去了該去的地方;二也是,他們本來就是疏離的家人,彼此間並不怎麼親密。自祖父與伯祖一輩向下,各有二房和三房男丁,就像大樹發杈,再發成七八家,將個宅子擠得滿騰騰。從他落地,放眼望去,都是人,耳朵裡則是齟齬。他們家的人元氣旺,秉性強,就沒聽說有早夭的,生一口,活一口。放養著,從中挑一個寵慣,滿足為人父母的天性,其餘也不為不平,因為是大多數。他雖是這房獨子,卻不是那個被選中的,選擇多是隨機,沒有什麼理由,這才能說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