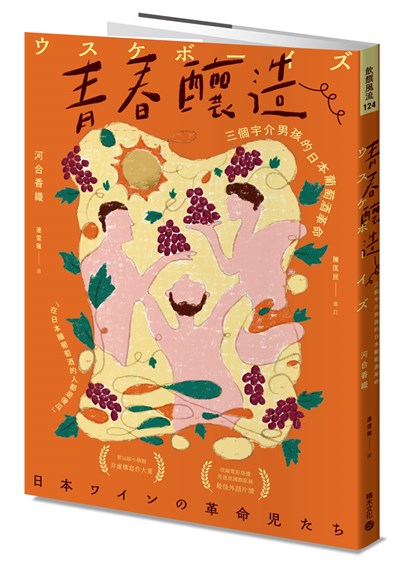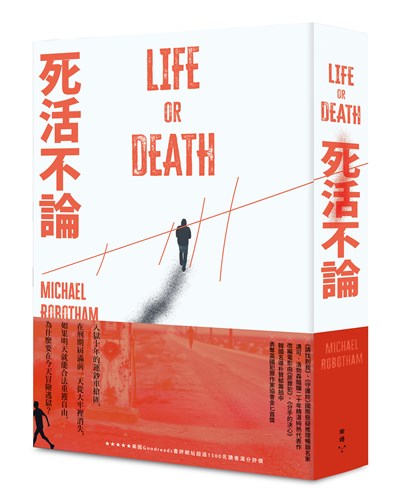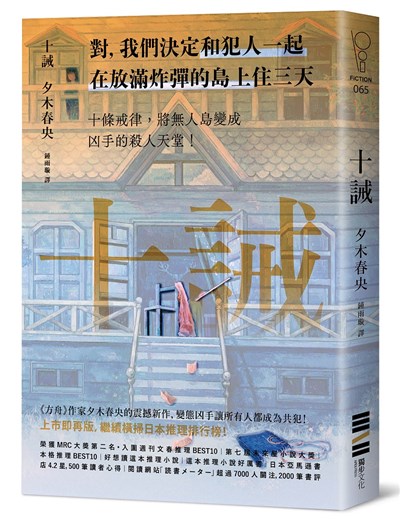日本統治、太平洋戰爭、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來臺……
這是國家如風中草芥的時代。
皇民、灣生、原住民、外省人、臺灣人……
這也是個所有人都不知何去何從的時代。
1940年代,日治時期的臺灣正逐漸步入陰影。彼時,八歲的梅子仍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島嶼北方,皇民化家庭的她,仍天真地為自己流利的日語還有被譽為當地棒球隊明日之星的哥哥感到自豪,尚不知戰禍一觸即發。
然而,當軍隊大舉進駐金瓜石,在近郊設立戰俘營,她的世界瞬間崩塌。那個懵懂樂天的女孩,隨著歲月流轉,看盡悲歡冷暖,終成滿頭白髮的老嫗。縱然七十年過去,戰時的負疚和罪惡感仍如影隨形,無法從她記憶中抹去。
往事靜默如金,這次該由誰開口訴說?
時代翻覆人心,施益堅試圖透過一個大時代中歷經四代的家族故事,叩問讀者關於歸屬感與認同。對於歷史洪流中的個體,過去已然塵封蓋棺,而未來的我們,又該如何直面這段歷史,真正去了解知道自己是誰?又經歷過什麼?
內容節錄
《梅雨》
她跑得飛快,以致眼前的世界模糊掠過。下坡,沿著宿舍間狹窄的小巷,把那些叫她要小心的人拋在身後。「梅子妳這樣跑,會摔倒的!」她的辮子從肩膀滑落,在她身後擺動。木屐踩在堅硬的地面上喀啦喀啦響。她的鞋子和衣服都不適合奔跑,但是到了山下學校附近她已經聽到觀眾興奮地竊竊私語,他們期待比賽趕快開始。她為什麼沒有早點出發?在最後一刻她決定到山上的神社祈求勝利。她走礦坑前平整的小路,然後左轉。在山下所長的住所旁邊有一道階梯通到村子裡。
她暫時放慢了腳步,高高的竹子遮擋了房子,那是整個金瓜石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如果太子賓館不算的話,那裡沒有人住,所以不算。有一次她父親在下班後必須送一件重要的公文給所長,帶她同行。所長家裡面散發檜木的味道,靠山谷的一側是一個精心打理的院子,裡面有一條白色礫石鋪成的小路和一個養滿金魚的池塘。像往常一樣,正門口停了一輛汽車,山下先生和他的妻子週末外出時,司機會載著山下夫婦到瑞芳火車站,或者山下太太要到九份逛街,司機也會載她去。沉默的司機總是穿著制服戴著白手套。
「梅子!」
以免在匆忙中絆倒或踩到蝸牛,她小心翼翼踩上最先的幾級階梯。地上因為之前的雨到處濕漉漉的。現在她停下來,抬起頭看到籬笆後面山下夫人優雅的身影。她左手撐著一把淺色紙傘,右手輕輕揮手。
「山下夫人……日安!」梅子鞠躬的時候,感到自己快喘不過氣來了,一時間她感到一陣暈眩。
「妳跑這麼快會跌倒的。」所長夫人面帶微笑地說。她身上穿著一件梅色的和服,繫著繡有茶花的腰帶,看起來一如既往的優雅高貴。就像古京都的宮廷貴族,梅子心裡想。
「因為……球賽。」她好不容易說出口。「我們對抗基隆的中學隊伍,如果我們贏了……」
她越是想平靜地說話,越是覺得喘不過氣來,而且她突然想到像在家裡一樣隨口喋喋不休是不禮貌的。「哥哥是先發投手。」她又補充說明,好解釋她的興奮。又一陣掌聲從學校操場傳上斜坡來。如果不是宣布了陣容,就是比賽已經開始了。
就算不高興,所長夫人也從來不會讓人察覺。柔和的春光透過竹葉,襯托出她白皙的肌膚和細緻的臉龐。聽說事實上她的家族來自京都,而且族譜可以上溯幾個世紀。「我聽說幾乎沒有人能擊中他的快速球。」她的回答讓梅子非常驚訝。她沒想到山下夫人會對棒球感興趣。所長家裡也會談論校隊和投球技術嗎?
梅子脫口而出:「如果他今天表現很好,說不定明年可以進臺北的高等商業學校,有一天還可以參加甲子園錦標賽。」
「真的嗎?妳一定為他感到非常驕傲。」山下夫人對待小孩子就像對待同類人,然而在金瓜石當然沒有她的同類人。當地的金礦屬於日本礦業公司,而且是全亞洲最大的金礦。她的父親說,如果沒有日本人,這裡會有一些冒險赤手空拳挖金子的人,就像從前一樣,然而這地方現在有自己的醫院、電影院還有兩所學校。順帶一提,最近報紙上有一篇關於敬治的報導,因為他完投了整場比賽沒有失分,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山下夫人知道的原因。報導中寫道他的快速球快如閃電,如春雷般擊中捕手的手套。片刻之間梅子感受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慈祥目光,忘記了著急。院子裡紫藤和蘭花已經盛開,黑色的鳳蝶四處飛舞。所長夫人再次抬起手說:「那就讓我們期待今天我們會贏,對吧?但是妳還是得小心,地面還很滑。妳身上穿著這麼漂亮的衣服,小心別弄髒了。」
「謝謝您,山下夫人!」梅子鞠躬彎腰大聲回答。她試著配合身上的服裝像個淑女走路,那是母親親手縫製的。一直到階梯中間,她才握起拳頭再次奔跑。在電影院後面,有一小片大海映入眼簾,如玻璃般平滑延伸到地平線。遠處有陣雨傾盆而下,但是山丘上飄著雪白的雲朵,而且異乎尋常地靜止在天空中,彷彿也想觀看金福宮旁運動場上正在進行的緊張賽事。這次是北部學區棒球錦標賽的決賽。
金瓜石初中這次晉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通常都是基隆和臺北的日本隊自己在北部一決勝負。都是學區很大的學校,那些高官富商的子弟習慣在最好的條件受訓。最近幾年大部分是臺北商業學校贏,但是敬治說在本賽季之前有兩名關鍵選手搬回日本了,而且補充說道:這是我們的機會。金瓜石連個像樣的棒球場也沒有,礦業公司的棒球隊在瑞芳打球。今天的比賽原本應該在中學的操場舉行,但是春雨過後操場淹水,梅子此時到達的場地是金福宮旁邊的運動場,屬於她就讀的小學。這裡也有很深的水坑,從遠處看彷彿地上到處放了鏡子。
她的心怦怦跳,擠過人群。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到了,還有一些家長,甚至和學校沒有關係的居民也來觀戰了。大家都親眼目睹她哥哥投的球讓對手陷入絕望。「不好意思。」她一邊喊,一邊拼命往前擠。要不是中途有人攔住她,她早就在開球前趕到和玲子(Reiko)約好的位置了。她已經聽到啪一聲,球落進捕手手套的響亮聲音,而且她很想踢所有擋住她視線的人的屁股。掌聲響起,有人大喊敬治的名字。還有幾公尺,她必須小心,不能弄髒衣服,同時留意她的好朋友在哪裡。如果碰到老師不能忘記行禮打招呼。在眾人頭頂上方隆起的綠色山丘三面包圍,猶如體育場的看臺。半山腰光禿岩石突起的地方聳立著紅色的神社鳥居──幾分鐘之前她從那裡跑下來,難怪她喘氣喘得像離水的魚。
「梅子!」這次是玲子從人群中大喊她的名字。她鬆了一口氣,舉起手揮了揮,不久之後她站在玲子旁邊終於可以看到球場了。她從來沒有看過操場上有這麼多人。因為比賽場地四周沒有圍欄,校長讓人拉起繩子圍住觀眾。
「我有沒有錯過什麼?」她喘著氣問。
「妳跑到哪裡去了?」
梅子沒有回答,而是伸長脖子。敬治筆直像個士兵站在投手位子,臉上流露全神貫注的神情。每次投球之前他會在胸前握住手套,那手套是因為他成績好爸爸送給他的獎賞,美津濃的真皮手套!下一刻他探頭好看清捕手給他的暗號。「這是第一個,對吧?」梅子沙啞地問。「第一個打擊者,我看不到牌子。」
「第一個已經被他三振出局了。」玲子回答道。「快、狠、準。」
「啊,我懂,他又等不及了。」
「說,妳到底跑哪裡去了?」
「我拿一枚錢幣到神社去許願了。」她們對看了一眼,玲子輕輕撞了一下她的側邊。玲子也很想要有一個讓全校仰慕的哥哥,然而她只有弟弟妹妹,而且還不少。他們一家九口住在一棟很小的屋子裡,屋子位在鐵軌和大海之間。所以她們早上沒有一起上學,而是在校園碰面,然後放學後在操場對面的校門口道別。儘管如此她們還是最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