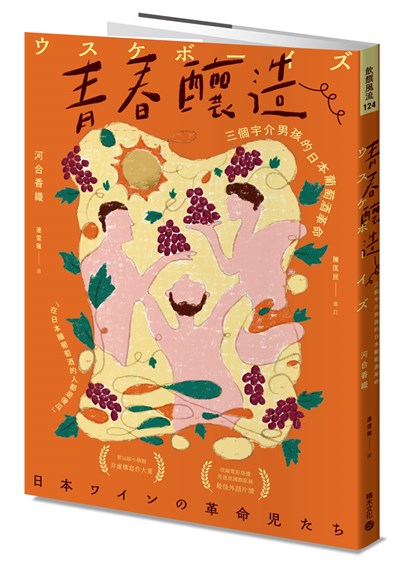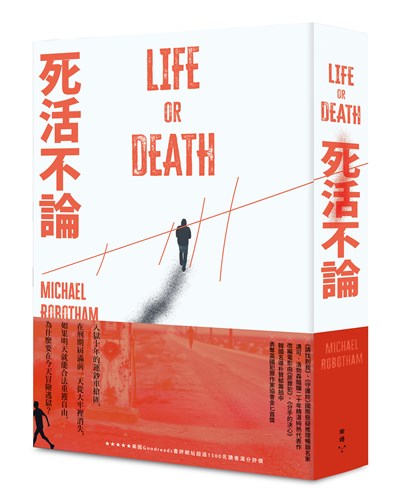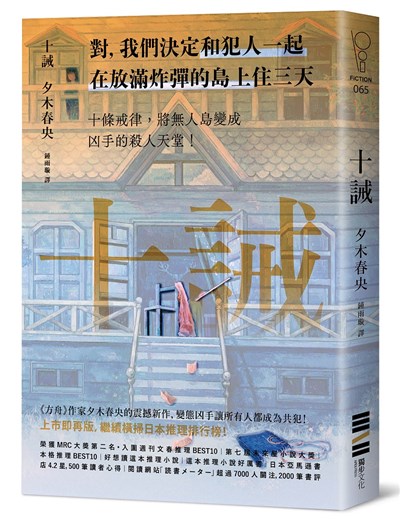全書以五名梁朝覆滅的主要人物:北朝降將卻起兵叛亂的侯景、無心政治卻不得不攬起國家責任的太子蕭綱。號稱最有軍事實力卻作壁上觀的諸侯蕭繹。自認若非父親昭明太子早逝、自己才是血統純正的繼承者蕭詧,以及本書中心人物,造成這一切的老皇帝梁武帝。
自立為王、勤王平亂、寄情詩歌、異族締盟、殉國得道
國破城滅的最後五日,五個人五種權謀盤算。成王、成寇、成聖、成佛,成敗在心念轉瞬間。全書看似講歷史,實際卻談五人的機關盤算,重構史上最複雜且最黑暗的朝代。
內容節錄
《五衰:梁武帝的末五日》
倒數二日:岳陽王蕭詧
1.
出了一陣熱汗,終於讓我從這場暑寒錯織的大夢裡驚醒過來。我啜飲兩口宮人送上的藥膳,湯粥苦口,舌尖的酸麻感蔓延開來,簡直難以下嚥。
建康城陷落的同一日,我陷入一場突發的惡疾之中,每日持續著睡睡醒醒,昏昏沉沉,一下滿身大汗,一下又冷到顫抖。就這麼輾轉一個多月都還沒有完全痊癒。如今已經是初夏五月了,襄陽這一帶暖陽遍覽、照耀在這片綿延肥沃的雲夢濕地之上。我卻仍感渾身乏力、離不開自己的床榻數步。
在持續月餘的這場病氣風邪之中,我做了好幾個夢。夢別西樓醒不記,大多已經如彩雲如琉璃易散易碎,但剛剛臨醒前的這個夢,卻還記得異常清晰。
我身在一座蓊鬱扶疏的綠意城市裡,顯然不是中土的城市造景,到處是葛藤草蔓爬牆虎。觸目所及,除了千萬疊重宮殿,就是浮屠伽藍。且氣候炎熱,男女衣著,亦悉如異人。襬紗婆娑,長裙曳地,飄飄然如仙人天女。
我在經籍裡讀過這樣的記載—「土地沃壤,花果茂盛」,「氣序和暢,風俗淳質」。雖然我從未去過,但我在夢裡知道這是位於天竺的毘舍離城。
我雖在病裡,夢魂卻來到了毘舍離城,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在佛經故事裡想到與毘舍離城有關的,那必然就會想到維摩居士。
相傳維摩居士來自於久遠劫,他曾供養無量諸佛,善根深厚,深諳佛理。不僅為百姓所尊崇,上至帝釋、梵王與世主,下至臣民,都曾受其教化。而《維摩詰經》最知名的,就是文殊菩薩往問疾的故事。
佛陀在毗舍離城施行教化時,得知病中的維摩居士期盼佛陀派弟子慰問,佛陀先請大弟子舍利弗、目犍連前往,他們卻紛紛推卻,原因是擔心在佛理上辯詰不過維摩居士。最後佛陀只得指派文殊師利菩薩率領眾菩薩、弟子五千人前去探病。在維摩居士的丈室之中,文殊菩薩問起居士患病的起因,維摩居士說:「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眾生病我亦病,眾生不病我病除。這不就是賢君聖主的襟懷嗎?我當然明白佛家說的眾生平等,但人生來有貴賤,社會不公平,而不公平建立在不同背景、身世的人,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與責任。
我是蕭詧。在分封岳陽王、統領襄陽雍州之前,我就已經是梁武帝蕭衍的嫡孫,是昭明太子蕭統的嫡子了。我有這樣的義務,也有這樣的使命。因為我身在大梁宮牆之內,身為蘭陵蕭氏的正統血脈。
眾生病時我也跟著病,直至眾生病癒的那一刻,我才能病除。這是我在這場夢境裡福至心靈的體會。也就在這將醒未醒的一瞬間,我體會到了前些時日的惡疾裡不曾感到的舒適與清涼。
我並不特別篤信釋家之說,但少年時跟著父親與祖父,認認真真讀過好幾年的空性與佛理。佛家說相對於火宅三界,淨土是無垢而清涼的。我想如今的清新體會,大概就是淨土了。
我的祖父梁帝蕭衍這幾年信佛崇法,可說是過了頭,我早就看出來,但他對佛理的體悟或許還不如我的父親蕭統。據說父親的少年時期就已經能在文德殿裡,解講二諦觀。在我童年的記憶裡,父親不特別重視梵唱、三寶、禮佛這些典章儀軌,但他跟我說過的那些故事、睡前的童話,總是有著靈光乍現的處處禪機。
雖然父親離世已經將近二十年了,但我還是經常想到他的身影,他頎長但不至於瘦弱的身軀,以及說話時像怕吵醒孩子般、又似喃喃自語的輕嚅。
「譽兒,詧兒,你們聽過香象渡河這個故事嗎?有一天有三隻動物,兔子、馬與大象,來到天竺國最大的河流—恆河的岸邊。這三隻動物決定比賽誰先渡過這恆河。你們來猜猜看,這場比賽,牠們三個是誰贏了呢?」
記憶裡那時我大概才四五歲吧?大哥蕭譽與我同年,比我大幾個月而已。而父親也還很年輕,眉角清朗,臉龐光滑,下頜還冒著青白色的鬍渣。
我是怎麼回答的呢?駿馬在陸地跑得最快,但在河裡則不然。脫兔動作迅猛,在河裡應當也是如此。至於笨重的大象,我只有在佛經畫冊裡看過。
我當時應該是說了某個答案,但父親沒有肯定也沒有否認。
如恆河水,三獸俱渡,兔不至底,浮水而過;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則盡底。(《優婆塞戒經》)
我後來才知道這個佛家故事。因為脫兔身軀矮小,所以全程踩不到河底,只能浮水而過;駿馬稍微高大,在岸邊之時、尚能踩到河底,但到了水深處則踩不到了;至於香象體軀巨大,步步都能盡踩河底,穩穩地渡過寬闊的恆河。
父親離世後我經常想起這個謁語,想到這個故事的寓意。父親要問的問題應該是—這三隻動物並不是誰比較快,而是誰走得比較穩。
「詧兒,你知道嗎?你如果要當、就要當那隻渡過恆河的大象。」在那樣一個斜陽映射的魔幻時刻,父親端坐在他的盈牘累箱的几案前,看著他案頭那些浩繁的書軸譜卷,沒有抬頭,但語氣卻異常溫柔—「有一天你會知道這條河有多深,大海又多寬闊。」
我腦海裡浮現那一條寬闊無邊際、澄黃燦燦的恆河水,滾滾泥流,粒粒沙數。而那隻香象依舊矗立在河水中央,深不見底的位置。巍峨不動,屹立不搖。
有一天我將成為那隻大象。在其他動物都浮空划著水的時候,我穩穩踩著自己的步伐。無論將來歷史如何記載,眼下時局如何波濤。
「來人,協助本王梳洗下床。」該是做些正事的時刻了。我對外喊了兩三聲,似乎時辰還太早,並沒得到回應。
我從年輕開始就慣於獨自就寢,無論是東宮裡那些保母乳娘,或體貼的書僮侍妾,我都不慣讓他們在我房裡伺候。君王有句流行語—「臥榻之上豈容他人安睡」,哈,我這可不是天生的帝王格局呢?
不過就在這小小幾尺的臥榻之內,酣然安睡的人太多了。當然,我說的是政治上的隱喻。即便在病中,但畢竟海內發生這等大事,我不得不去思考著大梁這塊小小版圖、半壁江山裡的動靜了。
我的兩個叔叔—湘東王蕭繹,武陵王蕭紀的實力不必多說了。就算我那幾個堂弟—蕭大連、蕭大心,就連還沒成年的蕭大圜都已經晉封了南郡王。他們隨時都能威脅到我。
文殊菩薩拜訪維摩居士,這是什麼預知呢?是否我會迎來預期之外的訪客,有了另外一次選擇的機會?
今晨的夢讓我徹底從病厄的昏沉裡清醒了過來。接下來要思考的,就是我大梁朝的未來,這是我們家族必須承擔的。此時假若父親還在,他就將繼承帝位,而我與蕭譽就會是理政監國的國之副貳……這本來就該是我們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