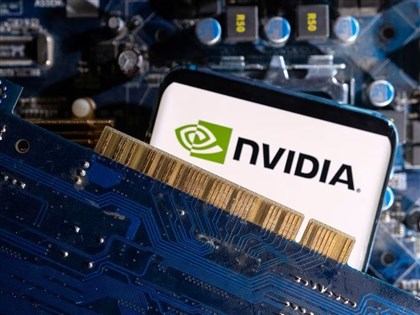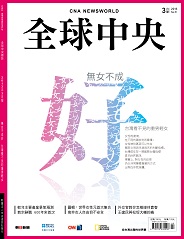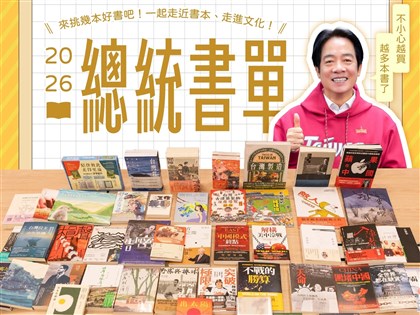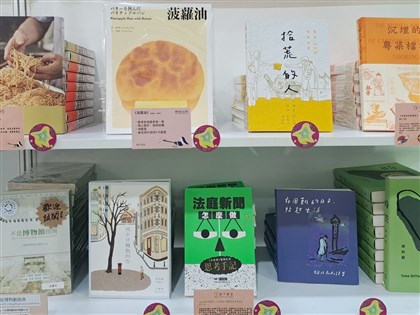紅旗落下後的俄羅斯
俄羅斯總統普丁曾感嘆地說:「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普丁的話,說明了當代俄羅斯人對於蘇聯過往歷史的緬懷與自我矛盾。
文、攝影/李孟遠 (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俄羅斯人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彌賽亞精神:他們的祖先以巨大的犧牲抵禦了蒙古鐵騎對於歐洲文明的破壞,粉碎了拿破崙、希特勒稱霸世界的野心;俄羅斯民族拯救了全世界。
正是這樣一種使命感,1917年在列寧(Vladimir Lenin)的領導下,共產黨推翻了自由主義政權的臨時政府,在俄羅斯大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這是俄羅斯民族一次大膽的嘗試,因為這次他們必須自己定義未來的道路,而不是照抄西方。
15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面共產主義大旗的號召下,共同組成一個橫跨歐亞、在世界政治舞台呼風喚雨超過半個世紀、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蘇聯。
這是自18世紀俄國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來,俄羅斯首次成為全球霸主。俄羅斯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那個歐洲人眼中落後的農奴制國家;蘇聯的影響力深入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紅色角落」。
然而,正如同世界歷史上所有強盛的帝國最終都將傾倒一樣,1991年底蘇聯走到了它生命的終點。誰也沒有料到這個社會主義祖國,竟然就在一夕之間分崩離析,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對於蘇聯的解體,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曾感嘆地說:「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普丁的話,說明了當代俄羅斯人對於蘇聯過往歷史的緬懷與自我矛盾。
「蘇聯制度的優越性在哪裡?─成功地克服了在其他社會制度裡不會存在的困難。」
以上是一則挖苦蘇聯社會主義的笑話,然而,對於多數的俄羅斯人來說,1991年蘇聯的解體,並沒有解決紅色帝國留下來的問題,新的困難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逐漸浮出檯面,形成了俄羅斯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尤其是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文化,深刻地影響著這個劇變中的大國。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宮飄揚超過一甲子的蘇聯紅旗緩緩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帝俄時期的國旗─象徵斯拉夫精神的白、藍、紅三色旗,俄羅斯開啟了歷史的新頁。
然而,此時的俄羅斯民族對於未來的道路仍舊徬徨,不知該走向何方。一切又回到原點,在共產主義此路不通的歷史教訓下,俄羅斯嘗試面向西方民主道路,力圖雄風再振。而這次主導俄羅斯國家前途的人物,正是蘇聯的掘墓人─葉爾欽(Boris Yeltsin)。
葉爾欽領導下的俄羅斯亟欲向西方靠攏,試圖透過「震撼療法」,將俄羅斯帶往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令人遺憾的是,葉爾欽的「震撼療法」失敗了,國家的巨大財富落到少數投機分子手裡,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階級對立更加激烈,俄羅斯淪為三流國家,民族自信心跌入谷底,一蹶不振。
同一時間,資本主義也以銳不可擋的速度,滲透到俄羅斯社會當中,人們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渴望日漸加深。
2000年,普丁從葉爾欽手中接下權力的手杖,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特務頭子,躍升為俄羅斯最有權力的人物,並誓言將俄羅斯帶往大國復興的道路。
在普丁的鐵腕統治,以及受惠於石油、天然氣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下,俄羅斯開始從葉爾欽時代的混亂中恢復秩序。2012年,儘管社會批評聲浪不斷,普丁第三度當選俄羅斯總統,開啟了新普丁時代。
如今,當人們漫步俄羅斯街頭時,即使是在偏遠人口不多的小鎮,也能輕易發現麥當勞以及其他歐美企業的蹤跡,俄羅斯愈來愈像歐洲國家。然而,即使在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後,俄羅斯還是令人難以理解。
俄羅斯不像它的歐洲鄰居那樣,強調個人的自由,有時還認為這種自由是有害的,秩序與平等遠遠比是否擁有自由重要,集體主義成為貫穿俄羅斯社會的主軸,並從根本上決定了俄羅斯人的行動準則。
舉例來說,在俄羅斯,行政效率不彰時常為人所詬病,無論是政府機關或是私人企業,經常存在著蘇聯式的官僚主義:數個不同單位負責同一件事,一旦出事卻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這不禁令人想起19世紀俄國詩人秋切夫(Fyodor Tyutchev)對於其祖國的描寫:「俄羅斯不能只用腦袋來理解;尺度無法衡量她,因為俄羅斯有著特別的軀體;俄羅斯只能信仰。」
俄羅斯作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多民族國家,東西方文化在此發生碰撞,孕育出獨一無二的俄羅斯文明。蘇聯在上個世紀的解體,並不意味著俄羅斯人對於這段歷史的否定,而是暫時停下腳步,對於未來進行重新思考。正如同俄羅斯的國徽─雙頭鷹所象徵的,同時注視著西方與東方,俄羅斯注定要做一個歐亞大國。(完)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