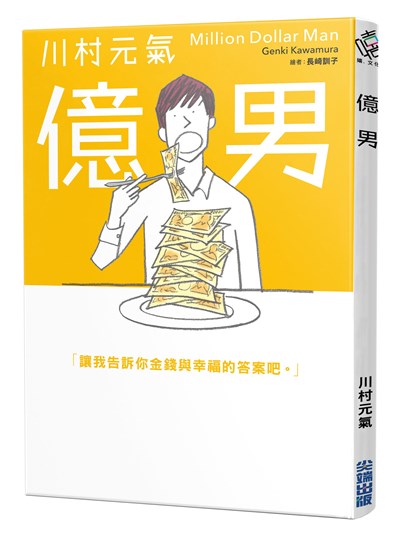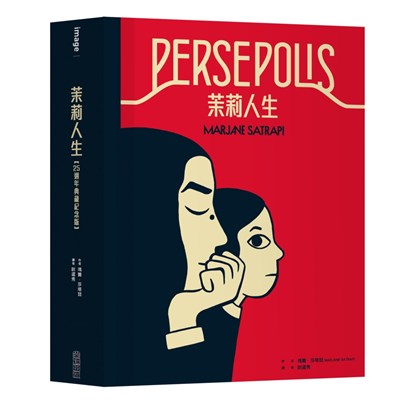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奪走小男孩的生命,肇事者卻冷血逃逸。悲痛的父親法蘭克陷入絕望與憤怒,警方久查無果,他決定親自追凶報仇。
就在他被復仇吞噬之際,一封封匿名恐嚇信接連出現,暗示有人在監視他。法蘭克隱姓埋名、設計完美謀殺,卻在行動當天意外失敗,可是目標卻仍然死亡。
被懷疑為真凶的他只得求助私家偵探奈丘.史川吉威調查,揭開一場更深層的陰謀與殺機。
內容節錄
《野獸該死》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我要殺了一個人。那個人叫什麼、住在哪裡、長什麼樣子,我一概不知。但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後殺了他……
仁慈的讀者,請原諒我用了這麼戲劇化的開場。是不是很像我寫的偵探小說的開場白?唯一的差別是,這個故事永遠不會出版,而「仁慈的讀者」也只是習以為常的禮貌說法──不,也許不盡然。我打算幹下這世界稱之為「犯罪」的事,而每個罪犯都需要傾訴的對象,如果他沒有同夥的話。那種孤孤單單、與世隔絕、懸著一顆心的感覺,沒有人承受得了。說溜嘴只是遲早的事。就算意志再怎麼堅定,超我也會背叛他。膽怯也好,自大也罷,心裡的衛道之士都會不斷追著雞鳴狗盜之徒跑,逼得他說錯話,害得他輕忽大意,布置不利於他的證據,像個誘捕教唆的密探。雖說法治的力量再強大,遇到毫無良知的罪犯也沒轍,但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股贖罪的衝動。罪惡感就是出賣自己的內賊。心裡過不去的事,就會反過來背叛我們。就算嘴巴不肯說,行為也會不經意透露。這就是罪犯喜歡回到犯罪現場的原因,也是我寫這本日記的原因。而你,我想像中的讀者,偽善的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兄弟1,你就是我的告解對象。我會對你全然坦承。若有人能拯救我免於走上絞刑台,那個人就是你。
坐在這裡想像謀殺案很簡單。我情緒崩潰之後,詹姆斯就把這間小屋借給我靜養。(不,仁慈的讀者,我沒發瘋,你大可以拋開這個念頭。我的腦袋比任何時候都要清醒。我有罪,但沒瘋。)望著窗外的金頂山在夕陽餘暉下閃閃發光,海灣裡盪漾著有如金屬葉片一樣的波浪,卡柏港在我腳下三十公尺處,伸長了彎曲的手臂擁著一艘艘小船,要想像謀殺太簡單了。因為放眼望去盡是馬丁的身影。要是馬丁沒死,我們就會一起去金頂山野餐;他會穿上那件他很得意的大紅色泳衣涉進海裡戲水。今天就是他的七歲生日,我答應過他,等他滿七歲就要教他開小帆船。
馬丁是我兒子。六個月前的某天傍晚,他出門去村裡買糖果,卻在家門前的那條馬路出了車禍。對他來說,那可能只是轉角迎面而來一陣刺眼到讓人愣在原地的車燈;短短一瞬間的惡夢,之後的衝撞卻讓所有一切墜入永恆的黑暗。他整個人被彈到水溝裡,當場斃命,幾分鐘後我跑出去,只見糖果撒了一地。我記得我彎身去撿,一時之間不知還能做什麼,直到在其中一顆糖果上看見他的血。事後我病了好一陣子,腦炎、精神崩潰之類的。我當然不想活了。馬丁是我的一切,泰莎生下他就死了。
撞死馬丁的人沒停車,警察也沒抓到人。他們說,身體飛得那麼遠又傷成那樣,可見車子開過那個死角的當下時速超過了八十公里。他就是我要找到然後殺掉的人。
今天先到這裡,我沒辦法再寫了。
六月二十三日
小屋還是沒變。怎麼可能變?難道我期望牆壁流下眼淚嗎?這就是人類的傲慢,以為在心裡翻攪的痛苦會讓自然的面貌隨之改變,可悲的謬論。小屋當然不會改變,除了生命已流逝外。我看見馬路轉角立起了危險標誌。太遲了,一如過往。
提格太太很安靜。她似乎察覺到了我的情緒,或者她是為了我著想,慰問的語氣才像在探病。回頭想她那句安慰的話,我尤其覺得反感──嫉妒某人曾經那麼喜歡馬丁,曾經參與過一部分他的生活。老天啊,我是不是快變成想把孩子占為己有的父親?如果是,那麼謀殺確實很適合我。
……寫到一半提格太太跑進來,紅通通的大臉上帶著抱歉而堅定的表情,像個鼓起勇氣去投訴的膽小鬼,或是從聖壇領完聖餐回來的人。「先生,我實在做不來,」她說,「我不忍心……」甚至開始哭哭啼啼,嚇了我一跳。「做什麼?」我問她。「把東西送走。」她哭著說,把鑰匙往我桌上一丟就奪門而出。那是馬丁的玩具櫃鑰匙。
我上樓到兒童房打開櫃子。我要立刻動手,不然就別想完成了。我盯著玩具看了很久,無法思考。車庫模型、火車頭、只剩下一隻眼睛的破舊泰迪熊,這是他最愛的三件玩具。考文垂.佩特摩4的詩句浮上我腦海──
他在伸手可及之處放上
一盒籌碼和一顆紅紋石
一片在海灘上受盡風霜的玻璃
六七個貝殼
一瓶藍鈴花
兩枚法國銅板,一一精心排列
撫慰他悲傷的心
提格太太說的沒錯,是該留著,留著不讓傷口癒合。比起村裡的墓碑,這些玩具是更好的紀念碑。它們會讓我難以入眠,讓某個人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