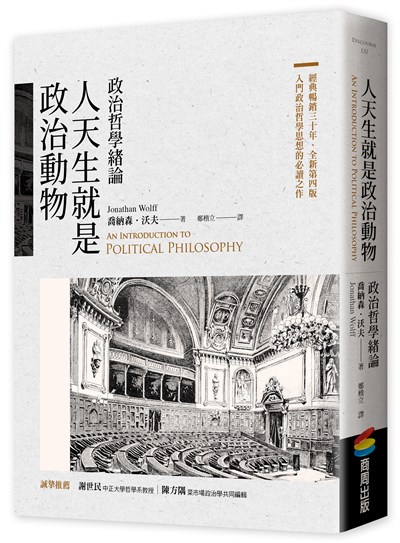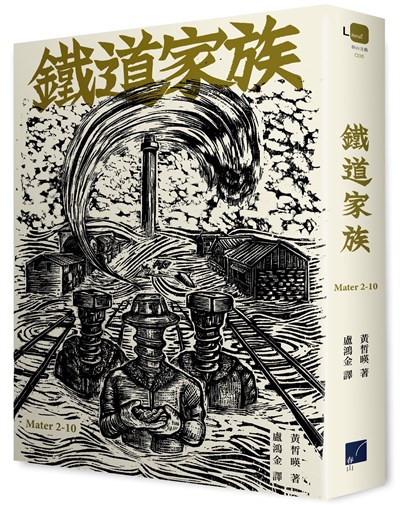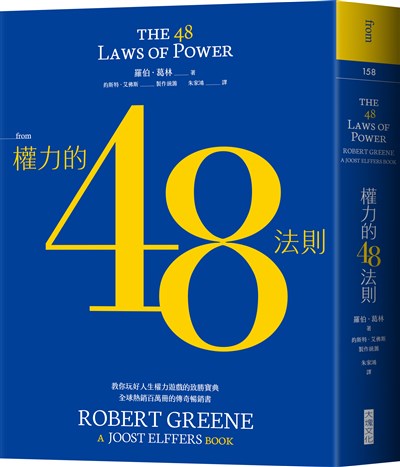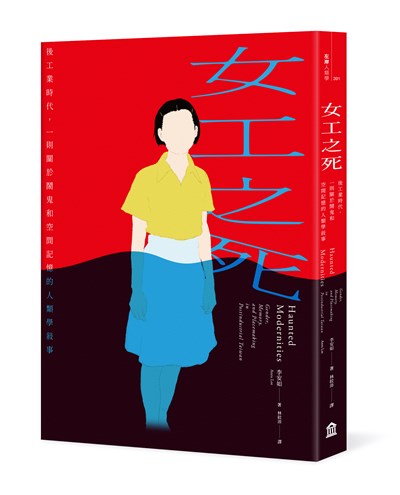
鬼魂不只是過往未竟之事的回聲,也是記憶政治的介入者。一九七三年旗津船難奪走二十五位年輕女工的生命,她們被合葬、被噤聲,成為未婚女鬼的傳說。《女工之死》以這座「二十五淑女墓」為出發點,揭示幽靈如何穿越時間與空間,在都市邊陲顯影,召喚那些被排除於主流歷史敘事之外的記憶與情感。書中描繪三方行動者——家屬、女權團體、政府——如何爭奪死者詮釋權,轉化鬼魂為神祇、為烈士、為文化象徵。這不只是對過去的追問,更是對現在的干預與未來的想像。
內容節錄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鬼魂、工業廢墟、記憶的物質性
第一次聽說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時候,我剛結束一個台灣工業發展與女性勞動力的研究,這個研究主要著眼於台灣經濟結構重整後,資本外流與去工業化對台灣工業腹地女性勞工的影響,接下來正準備將研究焦點轉向後工業城市如何作為全球經濟最新的資本積累地點。那時我在高雄進行民族誌田野調查,研究新自由主義經濟轉型以及同時施行的地方創生經濟策略(entrepreneurial placemaking strategy),如何改變高雄城市的地景與建築環境。當中山大學唐教授說起高雄女權會對二十五淑女墓改造所做的努力,淑女墓的故事立刻勾起我的好奇心。把整座墓地徹頭徹尾改造成公園,無疑是高雄市地方創生的一環。但是二十五淑女墓不只是單純需要改造門面的地方,它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二十五位未婚女性勞工的合葬地。逝者是未婚年輕女性,也是工廠勞工,她們的雙重身分讓二十五淑女墓開啟了民間文化宗教信仰與現代空間治理原則對話的可能性。
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Wolf)的經典文章〈神明、鬼魂、祖先〉(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認為,台灣漢人民間宗教的多神世界裡有神明、鬼魂和祖先三種存在,貼切反映出人間社會:神明是官員,代表皇帝和帝國,是公權力的象徵;祖先是父系家族的長輩,代表家族;鬼魂是陌生人或外人,人們會忌憚、但也鄙視祂們。性別是這個宇宙的關鍵要素之一。兒子生來就是父系家族的一員,有資格在父親的祖先供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死後自然成為祖先,但是女兒沒有這種特權。從父母的觀點來看,女兒只是父系家族裡的暫時成員,終將成為外人。因此,婚姻制度對女性格外重要,是女性前往她在漢人親屬制度中最終位置的象徵與通道,儘管這仍然是個從屬於男性的位置。一般情況下,女性要透過婚姻才能被丈夫的家庭接納,永久成為夫家的家族成員。因此女性如果尙未結婚就死於非命,又沒有經過適當的禮俗祭拜,就有可能變成無家可歸的鬼魂。婚姻也讓男男女女有機會生兒育女、延續家族,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相當比例的人會將沒有後代視為不孝。就經濟角度來說,婚姻還帶來一定的財務支持和社會保障,此對女性尤然;當代仍有不少人認為男性應該負責養家,男性也擔起了家中經濟支柱的角色。宗教、精神面加上經濟、物質面,種種考量讓一代又一代的台灣父母無不急著為兒女尋找良緣佳配,這是為人父母的重責大任。
在上述種種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安葬二十五名未婚女性勞工的淑女墓被視為無處可歸的鬼魂聚集之地。同時,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看,旗津二十五淑女墓也可比擬為鬼魂縈繞的「工業廢墟」(industrial ruin)。「工業廢墟」一詞本是用來描述資本主義地理變化下荒廢的工業遺址,作為一處已經停止運作的、荒廢的邊緣地景,工業廢墟削弱了場所中空間配置、法規執行、依規行事等種種秩序的管理規範。這些空間因此成為「將城市實踐的詮釋從日常束縛中解放」之地,進一步來說,這也提供了機會,讓大家「挑戰與重構烙印在城市的權力印記」。
旗津二十五淑女墓恰恰類似擁有雙重意義的工業廢墟。一來,二十五淑女墓是「勞工」的合葬地,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廢墟,因為勞工的死亡似乎象徵了高雄從工業化港口城市到後工業城市地位上的轉變;在此,地方創生是復興高雄後工業城市經濟的主要策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墓地」也是一種廢墟,因為它雖然是日常生活世界、城市地景的一部分,卻是已經不再活躍的那個部分。墓地通常位於城市邊緣,由管理人員負責維護,除了家屬掃墓,只偶爾會有路人無意間踏入。城市的日常運作基本上繞開了墓地,墓地並不屬於城市的有效迴路與生產結構之中。因此,墓地好比廢墟,喪失了立即的功能或意義,但又保留了引人聯想、不穩定的發聲潛力——埋骨長眠的墓主不用再遵守世俗的規則,祂的發聲因而得以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