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憤怒孵化溫柔的模樣 楊力州回首紀錄片25年來時路
最困難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說故事,讓它有強度跟意義……
文:王心妤/攝影:鄭清元/圖片提供: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影音:洪凰鈞
楊力州闖蕩紀錄片圈25年,是台灣紀錄片史上最多作品登上院線的導演。他的拍攝題材多是為弱勢族群發聲,失智症、特殊行業女性、偏鄉孩童都可以是電影中的主角。但楊力州一開始也和一般文青相同,只對國外的電影大師有興趣,直到「月亮的孩子」闖進他的世界,才讓他感受到紀錄片的衝擊力。
楊力州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樣溫柔卻有著清晰邏輯,思考時眉眼會微微靠攏,顯得有些憂鬱,雖然語句中仍會夾雜幾句玩笑,讓訪談氣氛不至太沉重,但他也曾有深陷憂鬱症的低潮。
雖然訪談中語調輕柔,但楊力州卻認為「憤怒」才是驅策紀錄片完成的重要動力,如何將憤怒作為土壤,種出能夠感動觀眾的花朵,楊力州有著獨門秘方。
走到紀錄片導演之路25年,支撐楊力州繼續拍攝的不是獎項或是票房,而是觀眾曾給予的一段話,讓他在哄堂大笑的學生們面前,淚流滿面也會藏在心底的一句話。
文化+:力州導演從一開始接觸電影,就愛上紀錄片嗎?對導演而言,第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紀錄片是哪部?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其實我小時候不太接觸過紀錄片,回想起來一開始接觸的大概都是拍世界大戰、動物生態或是蔣公多偉大。但我記得大二還是大三某個夏日午後,電影社同學跟我們系辦借了投影機放電影,同學說導演會來。對大學生來說,連導演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但聽到導演會來,就充滿期待。
記得那是308教室,我站在後面,想說沒什麼搞頭就可以從後門溜走,對同學或是導演都不會太尷尬。但我就這樣站著把整部紀錄片看完,也參加了映後座談。那是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我沒想到紀錄片會有那樣的衝擊力,內容是在說白化症的家庭,一個母親生了白化症小孩,因為醫學知識的欠缺,媽媽會被人家說是不是跟美國人偷生或是上輩子作惡多端,那樣的語句放在現實不會太陌生,但在紀錄片裡就是那麼強烈且真實,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文化+:對現在的力州導演而言,劇情片會比紀錄片少了點衝擊感和魅力嗎?
楊:老實說我看了很多劇情電影,但會觸動我的機率非常低。當然過程會進入角色,也會被戲劇感動,但還是有個聲音說,這是男主角、女主角、這是一場演出。儘管劇情再好、演技再棒,梁朝偉演技再好,還是會知道他就是梁朝偉,反而是真實紀錄,不用非常大的情緒波動,但只是一個眼神或是眼角小小的淚痕,我就會非常容易被感動。我現在看戲劇已經沒什麼樂趣,想一想滿可憐的。(苦笑)
文化+:導演1996年推出首部紀錄片「三個一百」,至今已走了25個年頭,累積了25部作品。請問力州導演認為紀錄片最能打動人心或是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楊:我想每個人標準不一樣,對我而言是「真實感」。拍到最後會知道,絕對真實是不存在的,紀錄片是一連串被選擇出來的真實,我為什麼選擇拍這裡?為什麼這個時間點拍?為什麼剪接這段?產出的過程是一連串的選擇。
尤其對真實的定義其實很狹隘,絕對真實好像只剩電梯裡的監視器,這時代眼見為憑都不一定是真實的了,所以真實在不同時空會有不同的定義。
對我而言總要有個信仰,最重要的信仰是無論拍攝怎樣的題材,就算知道那是被選擇出來的,但撐起這些的是「誠實」。我必須誠實把我在現場看到、感受到的東西,透過紀錄並剪裁,讓觀眾感受到。
文化+:但這樣出來的成品會不會變得太過主觀或是有立場呢?
楊:曾有個老師跟我說,紀錄片導演要像「牆壁上的蒼蠅」,概念是要讓被攝者沒有意識到你的存在。但我不管怎麼努力都沒辦法變成蒼蠅啊!(笑)我那麼大隻,以前的攝影機又很大台,被攝者一定會意識到我,所以一開始選擇用剪接隱藏自己。
到了現在,如果有人說我的紀錄片不客觀,那我會問他:「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客觀嗎?」每個人位置立場不同,客觀本就不是絕對的詞彙,而是種相對關係。紀錄片跟新聞不同,紀錄片導演能夠選擇站立的位置,無論是物理或是關係上,新聞而是需要平衡,對紀錄片而言,客觀不是需要服膺或是追求的一件事。
文化+:導演曾說憤怒是拍攝紀錄片重要的元素,但我感覺導演拍出的作品都很溫柔,請問對導演而言這種憤怒還存在嗎?
楊:憤怒經過包裝表現的不一定是憤怒,有時的長相是冷酷、有時是熱情或無感,如果憤怒的長相就是憤怒,那就會跟八點檔很像。憤怒不盡然會表現在作品裡,但它會是驅動完成的重要原因。
就像我監製的「怪咖」系列紀錄短片「非法母親」,那是對台灣代理孕母制度的不滿跟衝撞,但看完整部電影,甚至會覺得是愛情電影。一名女主角準備生產時,她的伴侶是唸詩給她聽,你能想像嗎?唸詩耶!這些異性戀男性大概也要反省一下吧!(笑)
文化+:拍攝紀錄片需要發掘議題、找出切入點、打開被攝者心房,對力州導演而言,你認為最困難的部分是哪邊?
楊:最困難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說故事,讓它有強度跟意義。一個人的觀點或是美學標準,在30歲左右會定型,到了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自己,日本漫畫也會這樣演,天才小廚師的敵人都不是其他小廚師,這是老話常談,但事實真的如此。
至於打開被攝者心房,那沒別的!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夠久,一部紀錄片常是以年為單位拍攝。被拍攝的漸漸對攝影機產生免疫,忘記我們的存在,但這時才是我們的功課。
當他不在乎攝影機存在時,會記錄到很瑣碎但是動人的細節,這時反而是我們要保護他,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完全敞開了,當我們構築故事時,更應該為被攝者著想。
文化+:導演花那麼長時間去紀錄,對方敞開心房時,導演也要毫無保留接受,拍攝結束後會不會深陷在低落情緒中無法走出來呢?
楊:可能別人不同時期經歷的階段,我們會非常密集的在短時間看到。這種情緒沒有處理好就會反撲,這大概是一種代價吧!
有病就要看醫生。我不避諱說這件事,我服藥了非常長的時間,我的諮商師說:「哎呀!導演,你只要不拍紀錄片就會好了。」我不敢確定這是不是熱愛的事,但有些回饋會讓我撐下去。
文化+:導演拍攝紀錄片的生涯中,無論是得獎或是觀眾反饋,有特別印象深刻的嗎?
楊:很多人以為是得獎或是票房,但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因為我在大學教書,有次學生拍了跟玫瑰花有關的作品,報告前還神祕的來跟我要求希望能播10分鐘的長度。影片中,有個戴著花布斗笠的花農大嬸好奇問他們為什麼要拍這個,學生就說是要拍紀錄片功課,大嬸再分享曾看過「被遺忘的時光」,學生還在鏡頭後興奮大喊「啊!那就是我們老師。」我還想著:「哼!想討好老師我,怎麼可以打斷被攝者說話,看我待會怎麼電你們。」沒想到大嬸突然轉頭對著鏡頭說:「我從紀錄片裡才知道失智症,我們村子裡有個人也是這樣,原本都笑他老番癲,看了才知道『揪拍謝』。你們老師我不認識啦!他做這件事我只有佩服,在我心裡這是很棒的。」教室裡的學生哄堂大笑,只有我一個人淚流滿面。
每次剪接時,我都會跟剪接師說「這就是我最後一部紀錄片了。」他一開始還會勸我,但作品完成得到回饋後,我就會告訴自己:那就再拍一部吧!後來剪接時又會跟剪接師說一樣沮喪的話,他已經不想理我了。
文化+:對力州導演而言,紀錄片在人生階段的意義有改變嗎?
有段時間是呈現正義和公益,有時又發現公益無法靠紀錄片做到,有時又變成藝術作品,有段時間又變成反思自我。
可能年紀到了,創作對我而言有更多哲學跟宗教的反思,像我之前拍攝「前進南極點」。那時跟Discovery洽談時,我打趣說希望茫茫大雪中出現金剛經,他們崩潰大吼:「為什麼?」但因為2500年前的佛陀每天就是好好吃飯、好好穿衣服、好好走路,我們在南極也是這樣,還有研究1912年率領英國隊伍前往南極探險的領隊羅伯特史考特日記時,我無法確定,但我一直感覺到他知道挪威探險隊先一步到達南極點後,有不打算活著回來的念頭,我想呈現這樣的感受。人有求生的念頭,難道沒有求死的意志嗎?
這些定義不斷流動,但我現在有監製新人製作「怪咖」系列紀錄短片的身分,正義公益的衝撞,就交給年輕人吧。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82期「一部紀錄片救地球」- 楊力州回首紀錄片25年來時路,4/26出刊)
- 2026/02/02 14:11
- 2026/02/02 10:21
- 2026/02/01 22:14
- 2026/01/30 17:59
- 2026/01/30 17:00
- 2026/01/30 14:49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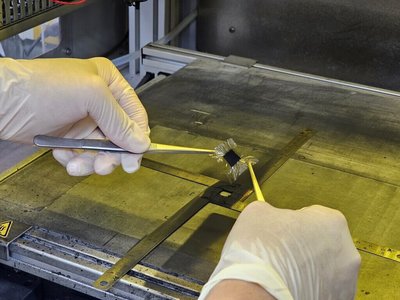





![獵魔女團Golden摘葛萊美 韓國歡慶K-Pop寫歷史新頁[影]](https://i.ytimg.com/vi/Qc2XNYDmV9M/hqdefault.jpg?t=2602030508)






